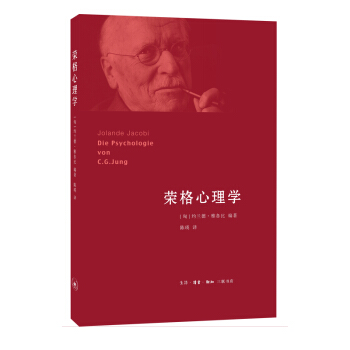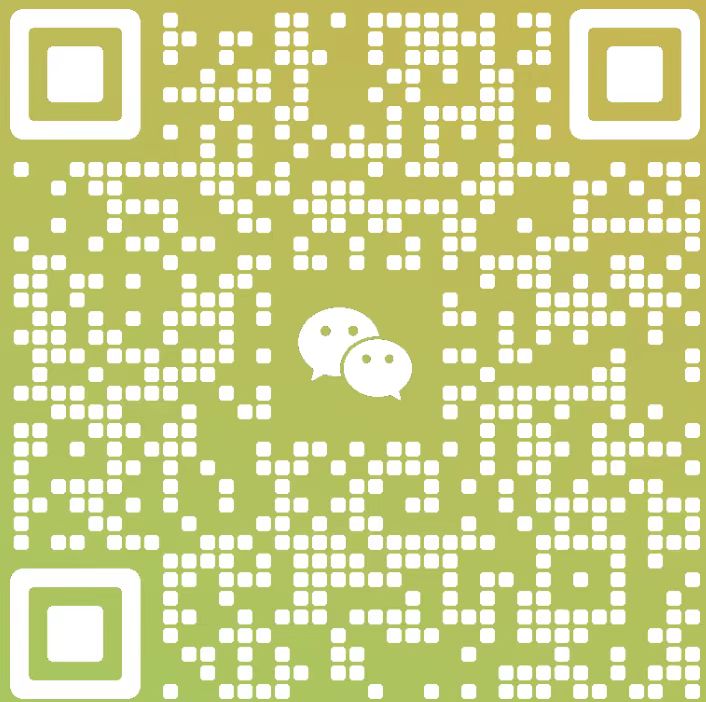第二次看这部电影了,居然泪奔了好几回。有很多片段,特别被打动,择二三记之,大概这就是文字和人文光芒的力量了。
1. 静坐听雨
老教授在下着暴雨且漏水的茅草屋教室里讲课,雨声如雷,学生完全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老教授尝试了几次大声重复之后效果甚微,索性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
“静坐听雨”
一种暂停键的诗意。
大雨击打在铁皮顶篷的声音,溅在土地水洼的回响,河里捕捞起来在网里蹦跳的鱼,雨中列队奔跑的体育系学生,镜头交错,到处是闪耀着的生命的力量。
回想起在高中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缺的就是这样泰然的老师,因为所有人都在催促着你前进,把你摁进书堆试卷堆,好像一切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这时候我反而喜欢给自己偷偷按个暂停键,晚自习混在大家的朗朗背书声里唱歌,下雨的时候望着窗外发呆写随笔,午休的时候不舍得睡觉看杂书听CD,写笑话集记录老师同学间发生的有趣段子。记得有次上课临时改为自习课,结果一阵困意袭来索性睡了一大觉,下课铃响后,当时的同桌兼当课课代表神色凝重看着我像看一个失足少年:你居然睡了整整一节课!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时看来奢侈的行为,因为时间是最宝贵的,我却拿来做一些对高考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对我自己而言,那些事情却是调节心态最好的方式,让我享受其中,那些是一段干枯时光里开出的花。最后也证明,这些“浪费”的时间也并非无意义,它让我感知丰沛,没有沦为一个书呆子。
2. 真实
“真实”这个词贯穿影片始终。
梅贻琦校长对当时迷茫的吴岭澜说:人把自己置于忙碌之中,有种麻木的踏实,但缺少了真实。
什么是真实?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不要忘记你们的真心和真性。”
在青春的迷茫期总会遇到一个问题——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不论是吴岭澜还是沈光耀,抑或你我,在内心的声音和合乎外界眼光下的正确选择之间,我们最终倾向了哪边?是否有“对自己的真实”?人生是条单向道,我们无法掉头重来,但是可以随时调整方向。我们可能无法决定终点和旅途的长度,但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啊。
吴岭澜在文科与实科选择迷茫之际得遇梅贻琦点拨,最终遵从内心。说来汗颜,回想自己高一文理分科之时,文理成绩比较均衡,而兴趣倾向于理科,对物理化学生物的解题如鱼得水乐在其中,而文科之中除了喜欢地理之外尤其讨厌政治和历史;然而当时的班主任和准文科实验班班主任都来游说我选择文科,理由是我的语数外三大主科成绩都很好,尤其数学,在文科生中会非常占优势,在高考中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大学。我还试图挣扎,结果班主任也是当时的物理老师又劝我说,别看你现在理科成绩好,到了高三女生就没有优势了,当时听了很是愤愤。
这便是因材施教遵从内心的教育和实用功利主义的教育之间的区别吧。至于最后纠结之余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文科,倒是源于一次父母的吵架,当时深感自己的劝和能力堪忧,心想索性从了文,练下口才也好。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高三做政治什么鬼的习题痛苦的要命的时候有。后来发现学了文之后口才还是不好的时候有,哈哈。
3. 人性的光芒
电影里空军教官说,“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正是这些精神,温暖彼此的善意,对于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气质,可以超越自然困苦,超越硝烟战火,超越邪恶黑暗,获得内心的磊落光明。
也正是这些精神,可以抵御集体疯癫,让文明得以延续,不让大厦崩塌。
面临战乱,偌大的北平容不下一张书桌,迁校云南,几校并立西南联大,在漏雨的校舍,在警报声中,在防空洞里,战乱动荡何其不幸;而集聚了各路大家畅所欲言交谈理想,拥有那么多的学术人生导师又何其有幸。影片结尾彩蛋浮现出的西南联大的时任教授,个个如雷贯耳、熠熠生辉: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华罗庚……在炮火和动荡中,他们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光芒万丈,优雅从容。
静水流深。能够在时间的长河里闪闪发亮的是发自本心的善意,是透彻的精神。有的人可能身无分文但心怀天下精神富足,而有的人可能一夜暴富但汲汲营营精神贫瘠。
影片中最被打动的一段是结尾:
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升的朝阳欢呼跳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甚至永远地忘了自己的珍贵。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
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打动我的是这种对自我珍贵的强调。我们常常在彷徨迷乱中怀疑自己,在不被理解中否定自己,却常常忘记了作为最独特个体的珍贵。这部片子给人以勇气,感动和力量。
保持内心的柔软和对生活的热爱,真正的英雄主义也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它。回首向来萧瑟处,看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仍会感动,热泪盈眶。
愿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们最终都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平和,愿所有平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都能安然着陆。
题外
这是部礼赞清华百年校庆的电影,也让我想到自己的母校,复旦。
大一的通识教育课程是最让我受益也是最享受其中的,那时候刷喜欢的教授的选课、听各种讲座成了最乐此不疲的事情。虽然是新闻学院的学生,却经常跑去听中文系哲学系等人文社科类的课程。
听外文系国宝级的老顽童陆谷孙讲有趣的俚语段子,哲学系如康德般冷峻严谨的张汝伦讲论语,中文系系宝骆玉明讲世说新语,社会学系大胡子曾奕讲西学经典,历史系网红教授钱文忠讲佛教史,哲学系小山羊胡郭晓东讲先秦哲学,等等。个个教授都极具个性又见解独到。
我们的官方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然而流传甚广最喜称道的民间校训则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我们奉为圭皋,这也是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上,我们唱着校歌泪流满面:“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然而现在独立思考的代价及阻力有多大,因为人总有一种趋于安乐的本性,包括我自己。比起痛苦地思索显然快乐地过好一天天比较轻松。而前两天刚在秦朔一篇文章中看到了一段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哲学界有个经典的题目是:你想成为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一只快乐的猪?有一个哲学家说,他会选择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因为比起猪的混吃等死,哲学家所拥有的深度思考能力,会带来更高级的愉悦。两者之间的幸福等级大相径庭。
随着上海文化地标季风书园最后一家的倒掉,公众的理性、独立、自由该何处安放。这家坚持“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的独立书店因为一个戏剧化的理由被迫关停。但看到市民们在书园的告别仪式不禁感动,书店被关掉但是“思想关不掉”,失去的是一个载体,精神在的话总有传承的渠道。如今再看书店创始人之前说过的这段话不禁有些唏嘘:
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未来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季风书园严搏非
季风怎么挡得住呢?待到盛夏时,又会带来湿润的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