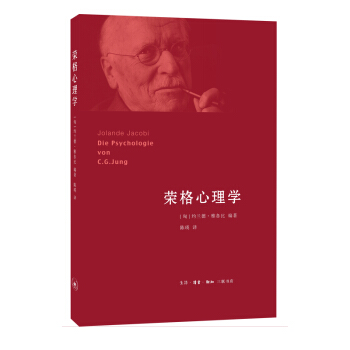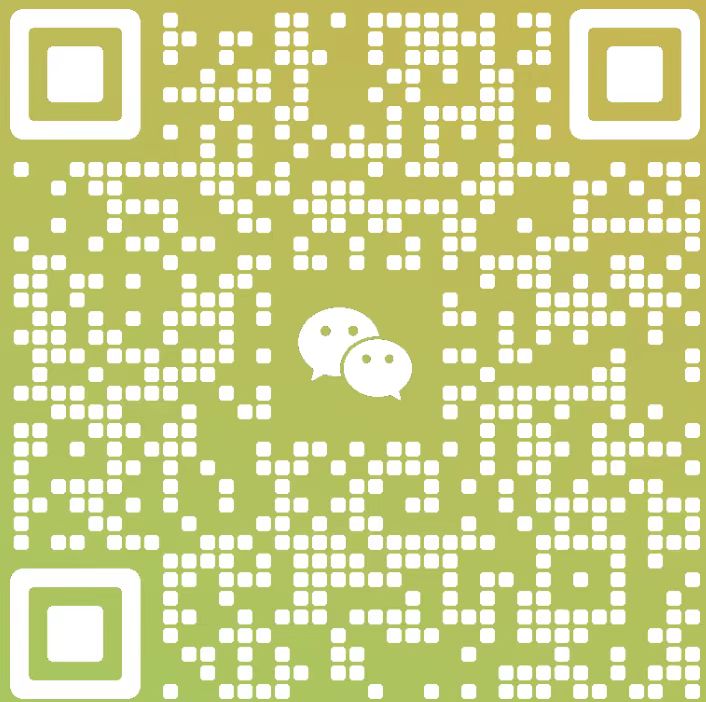个性化过程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发现“心象”。荣格把男人的心象称为阿尼玛,把女人的心象称为阿尼姆斯。心象的原型形象代表心理的异性部分,一方面表现个人与这个异性部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人类对异性体验的积淀。也就是说,心象是异性的意象,在我们心中既是单个的个体,也是一种类型。俗话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夏娃”。前面已经说过,按照心理法则,心理中一切潜在的、未分化的、未得到体验的东西,即无意识中的一切,其中也包括男人的“夏娃”和女人的“亚当”,都会被投射出去,所以我们常常在别人身上体验自己的异性本源,这和阴影没什么两样。我们选择一个别人,和一个表现自己心理特征的别人扯上关系。
像阴影和一切无意识内容一样,阿尼姆斯和阿尼玛的表现也可以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形式。内在的形式出现在梦、幻想、幻象以及其他无意识材料中,它们表现我们心理某一种或一整束异性特征;而外在的形式就表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异性人物身上,我们将他作为投射对象,把我们自己无意识心理的一部分或整个无意识心理部分都投射给他,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从外面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心象是一个或牢固或松散的功能复合体,如果一个男人喜怒无常,像女人一样感情冲动,或者一个女人对阿尼姆斯着了魔,自以为是,牢骚满腹,塀弃本能,以男人的方式作出反应,那都是他们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心象分开而造成的现象。“有时我们会在自己心中觉察到陌生的意志,它与我们自己想要的或赞许的一切背道而驰,这种意志的所作所为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它也可能有更好的意图,高瞻远瞩,赋予我们灵感,引导我们前进,成为我们的守护神,就像苏格拉底的精灵。”于是我们觉得,某人被一个陌生人“占领”了,就像俗话说的:“另一个灵魂进人了他的身体。”于是有些男人对某种特定类型的女人迷恋得不能自拔,我们经常看见偏偏是那些男性高级知识分子会不可救药地恋上娼妓,因为他们女性情感的一面完全没有分化;或者一个女人不可理喻地追随一个冒险家或江湖骗子,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心象的情形,梦中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是测试我们心理状况的天然尺度,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心象的表现形式简直是数不胜数。心象很少是清晰明确的,它几乎总是表现得含混复杂,带有所有相反的特征,但必须是典型的男性特征或典型的女性特征,比如阿尼玛可以表现为甜美的姑娘、女神、巫婆、天使、魔女、女乞丐、妓女、女伴、女斗士,等等,有些阿尼玛形象很有特色,比如帕西法尔传说中的孔德丽或珀尔修斯神话中的安德罗墨达,艺术作品中的阿尼玛形象有《神曲》中的贝阿特丽切、赖德?哈格德的《她》、伯努瓦的《亚特兰蒂斯》中的阿提尼亚,等等。阿尼姆斯的表现虽然不无区别,但也大致如此。较高层面的形象有狄俄倪索斯、蓝胡子骑士、花衣魔笛手,以及漂泊的荷兰人、齐格弗里德,等等,较低、较朴实层面的形象有影星鲁道夫?瓦伦蒂诺或拳击冠军乔?路易斯,或者在特别动荡的历史时代,比如现在,个别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将领也会成为阿尼姆斯,只要阿尼姆斯是个个人形象。此外,如果阿尼姆斯和阿尼玛还没有修成人形,还只是表现为纯粹的本能冲动,那么具有典型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的动物甚至物件也可以象征阿尼姆斯和阿尼玛。所以阿尼玛也可能表现为母牛、猫、虎、船、洞穴,等等,而阿尼姆斯也可能表现为雄鹰、公牛、雄狮或长矛、钟楼,以及任何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器物。
“心象的第一个载体大概总是母亲,以后才是那些激发男人感情的女人,不论那是正面的感情还是负面的感情。”脱离母亲是个性形成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尤其对于男人而言。为此原始人有一整套典礼、男人成人礼、转世仪式等,让那些刚成年的人有能力脱离母亲的保护,只有这样整个族群才会承认他们是成年人。而欧洲人必须在意识化自己心理的女性成分或男性成分时才能“认识”自己异性的一面。尤其是西方人,他们的心象,即心理中的异性形象,在无意识中埋藏得如此之深,所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的父权文明。“尽量压抑女性特征是男人的美德,女人也不喜欢被人看成女汉子。压抑女性特征和倾向必然导致这些需求都堆积在无意识中,女性意象也就必然成了这些需求的收容所,所以男人在选择爱人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想要赢得那个与他自己特有的无意识女性倾向最相符的女人,也就是那个能在最大限度上痛痛快快地接受他的内心投射的女人。”这样的男人娶的往往是自己最坏的缺点,这也能解释某些稀奇古怪的婚姻,女人的情形也一样。
在西方文明中,由于父权的发展,女人也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阿尼姆斯的力量。此外,现在有了控制生育的可能,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女人们减轻了家务负担,而且现代女性的才智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也都对此有所贡献。就像男人天生对厄洛斯缺乏信心一样,女人在逻各斯领域也总是缺乏信心。“面对阿尼姆斯,女性要克服的不是骄傲,而是缺乏自信以及对惰性没有抵抗力。”
像阿尼玛一样,阿尼姆斯也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光明的形象和黑暗的形象,或者说“上面”的形象和“下面”的形象,分别带有积极的性质和消极的性质。作为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中介,“阿尼姆斯的逻各斯原则决定了它重在认识,尤其重在理解,它传递的不是意象,而是意义”。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决定逻各斯原则的四个要素,都是以有意识为前提的。“意象被投射到一个类似于阿尼姆斯的真实的男人身上,他就承担起了阿尼姆斯的角色,或者这个意象也可能表现在梦中或幻想中,由于它表现了活跃的内心现实,所以它能自内而外地为人的行为染上特别的色彩”,无意识总是带有异性“色彩”。“处于更高层面的是非个人的阿尼姆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真正的灵魂向导,主持和陪护心理的转变。”当然,像阿尼姆斯和阿尼玛那样的原型,永远不会与一个真实的个人完全重合,而且一个人个性化程度越高,他作为投射对象与被投射的意象之间差异就越大,因为个性正是原型表现的真正对立面。“个性并非任何形式的典型,而是可能典型的单项特征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组合。”这种差异由于移情关系一开始是看不见的,但是渐渐地在投射对象的真实形象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最终的冲突和失望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无意识心理的各种成分和特征尚未分化发展并加入意识(比如一个人尚未认识自己的阴影),那么男人的整个无意识就都带有女性特征,而女人的整个无意识都带有男性特征,其中的一切似乎都染上了女性或男性色彩,荣格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索性称整个无意识领域为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如果人格面具过于僵化,也就是说只有一种主导功能得到了分化,而其余三种功能还都处于未分化的状态,那么阿尼玛当然就是这三种功能的混合体。但是随着分析的进展,两种辅助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阿尼玛渐渐地显露出最黑暗的第四种功能,即劣势功能的“完形”。如果阴影也还没有得到分化,也就是说,阴影还完全处于无意识深处,那么它往往会沾染上阿尼玛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梦中会出现一个阴影三人组,它们对应的是那三种无意识功能,而有时也会出现一个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三人组,阴影与阿尼玛之间的相互沾染在梦中也会表现为一个阴影形象和一个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形象之间的“成双成对”,表现为它们的“婚姻”。
一个人与他的人格面具认同程度越高,他的阿尼玛所处的环境就越“黑暗”,“阿尼玛被投射出去,于是大无畏的英雄也会惧内”,因为“如果对外不能抵制人格面具的诱惑,那么对内同样是软弱的,同样不能抵制无意识的影响”。一个对阿尼玛着了魔的男人,面临着失去“得体的”人格面具的危险,从而变得女性化。同样,一个对阿尼姆斯着了魔的女人,也会因为阿尼姆斯的“意见”,而丧失已成习惯的女性人格面具。这两种人的典型表现是“刻薄”。
阿尼姆斯很少是单个的形象,考虑到无意识内容对意识行为的补偿性,我们可以说:因为多配性是男人天生的外在倾向,所以他的阿尼玛,他的心象往往表现为单个的形象,这个形象聚合了各种复杂的矛盾的女性类型,所以真正的阿尼玛形象有着“变幻多端的性格”和“精灵般的本质”;而女人在生活中倾向于单配性,她们的心象就呈现出多配倾向,作为补偿的男性气质往往以各种不同的版本在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单个形象中得到人格化表现,所以阿尼姆斯是“多数”的体现,像是“父辈及其他权威的集合,他们的判断是权威性的、无可辩驳的、‘理智的’”。女人,尤其是那些以情感为主导功能的女人,她们的思维功能分化程度极低,她们之所以喜欢吵架和无理取闹,就是因为她们对各种意见、成见、原则不加批判就全盘接受,这是绝大多数女人的天性。这个比率相当高,但是自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这个情况已有所改变,由于心象与无意识深处见光最少的功能是重合的,所以它的性格与主导功能相反,并表现在一个与这种性格相吻合的特别形象中。所以,长于抽象思维的科学家的阿尼玛是浪漫情感型的;而耽于感官享受的世俗女人则是直觉丰富、神经敏感的艺术家的阿尼玛;感情用事的软弱男人心里装着女汉子的意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意象表现为女权主义者或女博士。女人的阿尼姆斯形象也一样,根据各人主导功能的不同,阿尼姆斯时而是危险的唐璜,时而是长胡子的教授,有时又是威猛的英雄,比如战上、骑兵、球星、司机、飞行员、影星,等等。阿尼玛并不仅仅是躲在无意识暗处伺机引诱的本能冲动的形象表现,而且象征着男人心中智慧、光明的引路人,这是无意识的另一面。这一面不是将他往下拉,而是将他往上推;同样,阿尼姆斯也不仅仅是厌恶一切逻辑的意见鬼,它还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多产的形象,当然它不是在形式上做男人的工作,而是发表有用的言论,它是“逻各斯的理性萌芽”。男性从内在的“女性特征”中产生完美的作品,而阿尼玛是他的灵感缪斯,“女性内在的男性特征所产生的创造性萌芽,能使男性的女性特征受孕”。通过这种方式,男女两性不仅在自然、幸福的身体结合中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赋予自己“身体的孩子”以生命,而且在贯穿并联结他们内心深处的神秘洪流中也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从中产生“精神的孩子”。如果一个女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懂得与自己的无意识“周旋”,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她就有可能成为男人的“女性灵感源泉”或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者、贝阿特丽切或悍妇。
如果男人到老来变得娘娘腔,而女人变得强悍,那就说明,本该转向内心并在内心发生作用的心理成分转向了外界,因为这些人没有及时给予内心应有的承认。我们只有在还没有看透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真正本性的时候才会迷恋他们,那时也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失望。但是对方的本性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看透,因为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找的就是能代表我们自己无意识心理人格成分的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把自己的错推给女性或男性伴侣,也就是说投射消除了,我们因此得以收回大量之前用于投射的心理能量,供自我使用。当然,投射的收回不能与大家所说的“自恋”混为一谈,虽然收回投射也是“回归自己”,但不是“自我满足”,而是自我认识。
一旦意识到并看透了自己内心的异性特征,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自己以及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这意味着我们在获得真正独立的同时也难免孤独,那是“内心自由”之人的孤独,这样的人再也不会受到任何爱情或伴侣关系的捆绑束缚。对他们而言,异性已经失去了神秘性,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认识了异性特征。这样的人也不太可能再“陷入爱河”,因为他们再也不会迷恋任何人,但他们能有意识地奉献更深沉的“爱”。他们的孤独并没有让他们远离世界,而只是让他们与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孤独,他们的本性得以牢固确立,这使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和睦,更无保留。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往往需要耗费半生的时间,不经过斗争大概谁也达不到这个境界。此外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其间失望也在所难免。所以,对付心象不是青少年的任务,而是熟男熟女的任务,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人到了人生后期才有必要关心这个问题。在前半生,两性结合主要是身体的结合,“身体的孩子”是结合后产生的果实,也是生命的延续;而到了后半生重心就转为心理的“结盟”,双方不仅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异性特征结合,而且也与外界的意象载体结合,帮助“精神的孩子”获得生命,使两人的精神存在获得果实和延续。
遭遇心象之日,也就是人生的前半部分结束之时,此时人对外界现实有了必要的适应,因此意识也确定了向外的方向,从此人必须开始进入适应内心的重要阶段,开始面对自己的异性成分。“所以,激活心象原型是命中注定的事件,这明白无误地宣告了人生后半部分的开始。”
我们在德国文学中可以找到非常优美的例子,那就是歌德的《浮士德》。在第一部分中,格雷欣是浮士德的阿尼玛的投射对象,这段爱情以悲剧告终,这迫使浮士德从外界收回了投射,他转而在自己身上寻找心理的这一部分,最终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在他自己的无意识“地府”中找到了,海伦就是这一部分心理的象征。《浮士德》诗剧的第二部分是个性化过程及其所有原型形象的艺术化表现,其中的海伦是个经典的阿尼玛形象,是浮士德心理的心象。他在各个阶段、各种转变中与这个心象周旋较量,直至出现了最高形象荣光圣母,这时他才获救,得以进入那个永恒的世界,在永恒的世界一切对立矛盾都消除了。
正如阴影的意识化使我们得以认识自己同性的阴暗的另一面,心象的意识化也使我们得以认识自己心理的异性特征。心象一旦得到认识和开发,它就不再从无意识中发挥作用,我们终于可以分化心理的这一异性成分,并将其纳人意识倾向,大大地丰富我们的意识内容,并进而大大地扩展我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