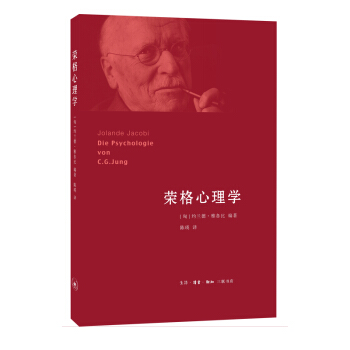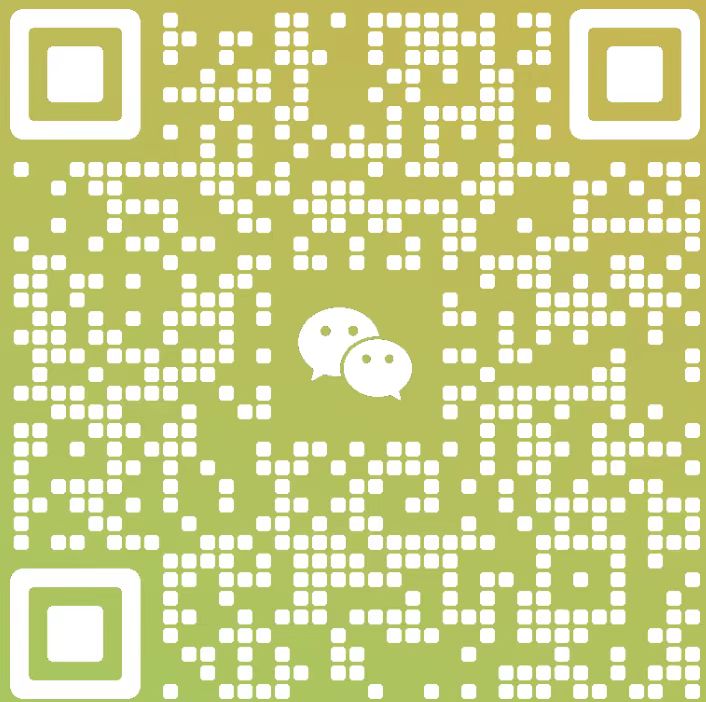从梦、幻想、幻象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很容易识别其中有多少个无意识的成分,又有多少集体无意识的成分。从神话性质的母题或人类历史上普遍可见的象征以及特别强烈的反应,我们可以推断最深处的层面已经参与其中。这些母题和象征对整个心理生活有着决定性的重大意义,行使着支配功能,充满能量和活力,所以一开始(1912年)荣格称之为“原始意象”,或者用J.布尔克哈特'的话说是“天然意象”,后来(1917年)荣格又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主宰”,直到1919年荣格才提出原型的概念。1946年以后,他将原型分为两种(虽然并未时刻强调):一种是“原型本身”(per se),它潜伏于每个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是不可感知的;另一种可感知的原型已经进人意识领域,表现为原型意象、原型想象、原型过程等,其表现方式常常发生变化,取决于其现身的具体情境。此外还有原型的行为、反应方式和原型的过程,如自我的形成等,还有原型的体验形式和忍受形式、原型的理解和理念,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原型会放弃迄今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作用方式,而走到前台行使其功能。原型不仅有静态的表现,比如原始意象,而且也有动态的表现,比如意识功能的分化。事实上,所有人类普遍的典型表现,不论是在生物学层面、心身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观念层面,都是以原型为基础的。原型或者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或者只属于或大或小的人群,据此我们可以绘制出原型发展的“阶梯状图谱”,就像一个家族的祖先一样,原型也可以繁衍出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却无损于它自己的“原始形态”。
本能就是在特定情境中,心理必需的反应绕开意识,以其天然的迫切性发起一种心理必需的行动,尽管外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心理必需的反应未必总是合情合理的。原型即是本能反应的映象,所以在心理事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黑暗的原始心理是意识的真正根源,而原型是其中本能现实的代表或人格化。
现在常有人提出质疑说,当今发达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后天获得的特性不能遗传。对此荣格的回答是:“这个概念说明的不是一种‘遗传的想象’,而是遗传的心理作用模式,就像小鸡天生就会破壳而出,鸟儿天生就会筑巢,马蜂天生就会用刺针攻击毛毛虫的运动神经,而鳗鲡天生就能找到去百慕大的路,所以说,原型是一种‘行为型式’。这是原型的生物性方面,是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但如果从内部看,观察主观内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的原型神圣而神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体验。如果这种体验披着象征的外衣,那么主体就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其后果是难以预见的。”
意识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元素,原型象征被别的内容所掩盖,中断了关联。我们的意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驾驭和控制意识内容,但无意识自有其稳定独立的秩序,不受意志左右,而原型构成了无意识的力量中心和力场,正是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陷入无意识的内容多次改道,并以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和意义,遵从一种我们看不见也意识不到的新秩序。如果我们懂得如何与这种内部秩序“打交道”,那么它会在我们遭遇意外和动荡的时候,为我们提供帮助和避难所。所以不难理解,原型能改变我们的意识观念,甚至使其走向反面,比如说,如果平日里完美的父亲在梦中变成了兽头羊腿的怪物或手抓一把闪电的、令人生畏的宙斯,温柔的爱妻在梦中变成了悍妇,那就说明,无意识在“发出警告”,它“更了解实情”,它想纠正错误的判断。
原型近似于柏拉图所理解的“理念”,只是柏拉图的理念仅限于“光明面”,只是尽善尽美的原始意象,与之对立的阴暗面就不能像“理念”一样进入永恒的世界,而只能留在生命倏忽而逝的人世间;反之,按照荣格的设想,原型具有对立统一的结构,光明面和阴暗面是其内在固有的两个方面。
荣格也将原型称为“内心的器官”,用伯格森的话说是“永远的未完成”。原型的“终极意义核心虽然可以界定,但它却无法描述”,因为“我们关于原型的一切具体解释和说明都来自意识”。如果我们还想再找一些类比,那么可以考虑最广义的“完形”,就是现在的完形心理学所理解的和生物学所接受的完形的意义。原型的决定因素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原型的形式,”荣格如是说,“就好比晶体的轴向系统,虽然它没有自己的物质形式,但是预先设定了母液中晶体形成的几何结构(原型本身),在离子及分子结晶的方式中,我们才能感受到轴向系统的存在……所以说,轴向系统决定的是单个晶体的立体结构,而不是具体形状……原型也是一样……虽然它的核心意义保持不变,但它只能是原则上决定自己的表现方式,却不能决定具体的表现细节。”这就是说,原型作为潜在的“轴向系统”,预先就已经理伏在心理的无意识系统中了。人类的体验就好比是母液,形成的意象凝结在轴向系统上,在无意识的怀抱中形态日渐丰满清晰。也就是说,意象上升时并不是刚刚“被生产出来”,而是早就已经理伏在黑暗中了,在它以典型基本体验的形式丰富人类心理体验宝库的时候就开始进驻无意识了。意象升人意识后,照射它的光线越来越亮,它的轮廓也就越来越清晰,直至所有的细节都暴露在强光之下。这个照亮的过程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尼采和荣格都确认了这一点,尼采说过:“我们在睡梦中学完了之前人类的所有课程。”而荣格是这么说的:“个体心理发育与种系心理发育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个推断不是没有依据的。”按照“形态理论”进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说遗传的“形态”以及“形态”中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都是可以感知的。“形态不需要解释,它体现的就是自己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原型想象视作化为意象的心理过程,是人类行为方式的原始模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会说:原型想象来自于对真实父母的体验;而柏拉图主义者会说:是原型造就了父母,因为原型是原始意象,是现实的楷模。个人生来就带有原型,它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固有成分,不牵涉个人的生老病死。“内心结构及其元素是否曾经生成,这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心理学无法回答。”原型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超越了意识。”荣格认为,若论本质,原型属于“类心理”,也就是类似于心理的领域。原型是“永恒的存在,问题是意识能否对原型的存在有所感知”。
原型可能在很多心理层面和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显现,以不同的“穿着打扮”和表现形式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和意义始终保持不变,像曲调一样,它是可以变频的。
一个原型母题或原型意象的表现形式越简陋、越模糊,说明该原型在集体无意识中所处的位置越靠近底层,在那个层面上,象征还只是“轴向系统”,还没有被个人的内容所充实,还没有被无穷无尽的个人体验的积淀所分化,也就是说,象征走在体验前面了。一个问题的时代性和个体性越是明显,原型现身时所穿的“外衣”就越是纠结、烦琐、明确,而原型如果体现的是非个人性的、普遍性的东西,那么它的表达语言就会非常简单而含混,因为就是宇宙也不过就是靠少数几个简单的法则建立起来的。同样,这种简陋的原型表现包含了世界和人生所有的丰饶和多彩,比如“母亲”原型的形式结构是预先存在的,统领一切“母性”的表现,这个原型的核心意义始终不变,它可以以所有“母性”的特征和象征充实自己,今人心中的母亲原始意象和“大母神”的特征,连同她所有的矛盾性格,与神话时代没什么两样。意识提升的第一步就是自我与“母亲”的分离。深化意识、表达理念,这是逻各斯的父亲原则,这个原则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一再挣脱母亲的黑暗怀抱,挣脱无意识。一开始二者本是一体,没有了一方,另一方绝不能单独存在,就好比在一个没有黑暗的世界里,光明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对立的两极保持平衡,世界才能存在。”
无意识的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原型在其中以人格化的或象征性的意象形式表现出来。“不论原型是什么内容,用的都是比喻的语言。如果原型以太阳为内容,并且将其等同于雄狮、国王、巨龙看守的黄金宝藏、人的生命力或‘健康力’,那么非此非彼,所有这些比喻表达的是不为人知的第三者,虽然这样的表达多少总有其贴切之处,但这个第三者始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可知之物,这是人的智力遭遇的烦恼……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幻想原型最终能得到解释和解决,最好的解释也不过就是把原型翻译成另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能贴切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原型的总数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数目很有限,因为它与人类自起源以来所获得的“典型基本体验的可能性”数量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原型的意义正在于它所表达和传递的“原始体验”。所有文明都拥有相同的原型意象母题,这是人类种系发育的结构决定的,我们在所有神话、童话、宗教传说和秘密宗教仪式中都能找到这些母题。“深海夜游”“流浪英雄”或“鲸龙”的神话与我们对日落日出永恒的意象化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斩杀巨龙的赫拉克勒斯、无数的创世神话、原罪、神秘的献祭仪式、童贞受孕、对英雄的无耻背叛、碎尸万段的奥西里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神话和童话都以形象化的象征形式表现了人的心理过程。同样,蛇、鱼、斯芬克司、助人为乐的动物、世界之树、大母神、中了魔法的王子、永恒少年、巫师、智者、伊甸园,等等,这些形象都代表某种母题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在每个人的个体心理中,这些形象可以觉醒过来,获得新生,施展魔力,浓缩为某种“个人神话”,堪与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创造的、广为流传的伟大神话相呼应,个人神话的形成过程,似乎也更为透彻地揭示了那些伟大神话的起源、性质和意义。
荣格认为,原型的总数就是人类心理中所有潜在可能性的总数: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庞大资源,其内容是关于神、人和宇宙之间深层关系的古老知识。在自己心理中开发这个资源,赋予其新的生命,将其整合到意识中,这就意味着消除个体的孤独,将个体纳入永恒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学知识了,而是为人之道。原型作为整个人类体验的原始起源存在于无意识中,并从这里发力干预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和义务。
作为他研究工作最后的成果,荣格在“共时性作为非因果关系原则”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指出了原型效应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科学对心灵感应、遥视,以及所谓的“特异功能”等ESP(超感官知觉)现象的解释,是非常不如人意的。而荣格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把大家至今不重视的、基至否认或称之为“偶然”的罕见事件和体验纳入科学观察和研究的范围。他所说的“共时性”(不同于同步性或同时性)是一种解释原则,是对因果关系的补充,他将共时性定义为“两个或多个内容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彼此并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在时间上的重合”。共时性的表现形式就是内心感知(预感、梦、幻觉、闪念等)与外部事件的重合,不论这种事件是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共时性都可能非常有意义,现在共时性暂时还只是一个“形式因素”、一个“经验性的慨念”,它假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知识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原则,并且“作为第四个元素加入了由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组成的三元组合”。荣格认为,共时性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无意识中存在有效的先验知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意识中那种知识的来源,而原型在其中是个发号施令的角色。共时性现象的本质是内心意象与外部事件的重合,这说明原型既有精神的一面,也有物质体质的一面。原型的能量负荷提高后,它的圣秘效应能让人兴奋激动,感情洋溢,造成意识水准的下降,这是共时性现象产生的前提。我们可以借用一句荣格的话说:“原型是通过内省可以识别的先天的心理格局。”这里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原型始终是生命中重要的精神力量,它要求得到认真的对待,并以奇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它始终提供保护和救助,如果它受到伤害,会造成‘心灵的危机’,这是我们从原始人的心理学中得知的,因为它无疑也是神经障碍甚至精神障碍的病原体,就像身体器官或机体功能系统受到冷落或虐待时作出的反应一样。”
原型意象和原型体验从来都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内容和宝贵财富,这不是没有缘故的。虽然原型脱离了最初的形式,嵌入了教义,但是在宗教信仰依然生机蓬勃的地方,不论是上帝濒死和复活的象征、基督教中童贞女受孕的秘密、印度神摩耶的面纱,还是穆斯林向东朝拜祈祷的仪式,这些原型无不凭借其含义丰富的内容和强大的力量,至今还在对人的心理施加可观的影响。只有在那些信仰和教义都已僵化,只剩下空洞形式的地方,原型才会失去魔力,无可奈何地把人遗弃在内忧外患之中,而我们这个高度文明、高度技术化、理性统治的西方世界就是这样的地方。
消除现代人的孤独与迷惘,把他们融入生活的大潮,帮助他们把光明的意识和黑暗的无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正是荣格心灵探索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在荣格的解梦理论中,那种被大家普遍称为象征的心理现象是极其重要的。荣格将象征也称为“力比多的化身”,因为象征转化能量,荣格将象征理解为适合于等值表现力比多的观念,它可以将力比多疏导到与初始状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中。以梦及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意象,反映了心理能量的本质和形态,正如瀑布不折不扣地表现了能量的本质和形态一样,没有能量,即没有物理力(但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假设),就没有瀑布;能量造就了瀑布,而同时瀑布又以其存在表现了能量的形态。如果没有瀑布,我们根本不可能观察和确定能量。这听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但矛盾正是一切心理现象最深层的本质所在。
象征既有表现力,又有改造力:一方面,它能形象地表现内心活动;另一方面,当它变成意象,“化身为”图像材料之后,又能以自己的含义给心理活动打上烙印,从而推动心理过程的流动。比如说,干枯的生命之树,象征着过于学究气的生活损害了人的天然本能,这个象征一方面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意义,并将其展示在梦者眼前;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展示,对梦者施加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为他的心理活动确定方向。象征是心理活动真正的能量转化器。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各个意象母题相辅相成。一开始这些母题还穿着个人经验材料的外衣,带有儿时记忆或其他记忆的特征,比如对最近发生的事的记忆。分析越深人,原型的作用就越明显,象征也就越能独自掌控全局,因为象征中有一个原型,一个抽象而带有能量负荷的意义核心。就像我们从画板上揭画,第一张画格外清晰,最琐碎的细枝末节都能看得很清楚,画的意义也很明确;后面的画细节越来越少,意义越来越不明确;直至最后依稀可辨的画,轮廓和细节已经完全模糊了,只能看见一个基本形式,但就是这个基本形式集所有的可能于一身。比如在“女性”的原型系列中,首先出现的是真实母亲的梦中形象,所有的特征清晰可见,其意义严格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范围内;这个意义拓宽、深化之后,形成所有作为异性伴侣的各式各样女人的象征;从更深的层面上升的意象带有神话的性质,那是仙女或巫婆;直至到达最底层的人类共有的集体的经验材料,那儿出现的是黑洞、阴间、大海,其最终的意义扩展为上帝所造生灵的一半、混乱、黑暗、受体。无意识中的这些象征,不论出现在梦中,还是出现在幻象或幻想中,就像在讲述一个“个人神话”,而在典型的神话、传说、童话中可以找到与“个人神话”最为类似的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象征是人类心理集体的(非个人的)结构元素,而且像人类身体形态的元素一样,象征是可以遗传的。”
“象征从来不是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而是无意识在觉悟或直觉的过程中产生的。”象征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内容,不论是自然过程还是心理过程,都可以用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日出日落,对原始人来说,这是外界的具体的自然事件,而对于对心理学有所认识的现代人来说,这可以体现人的内心世界同样有规律的活动。又比如“重生”的象征,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原始人的入会仪式,还是基督教早期的洗礼,或者是现代人的梦中意象,表现的总是精神转变的原始理念,只是完成“重生”的途径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历史的和个人的意识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想正确评估每一个象征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真正的意义,就必须从集体和个体的两个方面对每一个象征作出判断和解释。“神话意象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产生之初既有其客观环境,也有其主观环境,既与创造的产物有关,又与创造者有关。”个人关联和个体心理要素,总是对象征的解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